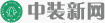“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大門打開了,但是小門還沒有開。”一位企業家抱怨說,社會資本在和地方政府的關系上,不少地方政府部門總是“留一手”,項目所在地政府永遠是強勢的。
1、股權之爭
股權之爭成為PPP模式推廣的“攔路虎”。對于PPP項目合作,不少地方政府部門明確表示,企業可以入股,但絕對不能控股,政府一定要保證51%的控股權。這令很多社會資本望而卻步。
“每次都是卡在控股權上。沒有控股權,我們的活力很難進去。”西南地區一位集團負責人說。該集團是香港主板上市的北京控股有限公司所屬旗艦企業,2010年,其與西南某省合作建設一些縣區的污水處理項目,方案是當地政府融資平臺投入8億元,集團投入10億元。這一方案幾經調整,始終無法獲得地方政府批準。
“PPP模式不僅是引入社會資本,也是引入更多的市場意識和現代管理理念。社會資本如果不能控股,項目就不能形成合理的公司架構,效率低下,無法有效運作。”一位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的企業家說。
還有企業反映,一旦項目出現重大問題時,地方政府即使控股少,也會動用行政手段進行干預,結果是社會資本“泥牛入海,受盡欺負”。
北京大學國家競爭力研究院研究員、中國PPP研究院執行院長郭建新說:“在多數PPP項目合作中,社會資本由于占股少,處于絕對弱勢地位。社會資本缺少決策話語權,參與PPP的積極性越來越低。”
2、調價機制不明
在PPP 項目中,由于招標時缺乏合理的成本預算作為標底,此時的服務價格并非依據行業平均成本確定,加上政府與企業存在信息不對稱,政府很難掌握項目公司的全部信息。并且由于缺乏人工、材料、機械消耗等統一的成本標準,使得服務價格往往因企業虛報成本而抬高。
在人力成本、材料成本迅速增長的形勢下,如果調價機制不明確,幾乎沒有民營企業敢在PPP項目上投入巨資。如果最后只是國企動、民企不動,這樣的PPP仍然是在體制內轉悠。
另一種情境相左的現象是,在服務費價水平不到位的時候,地方政府卻未能承擔起補貼責任。多位企業界人士稱,地方政府的支付意愿并不高。
關于城市基礎設施公共產品或服務的定價,存在一個客觀的矛盾,即公眾總是期望質優價廉的公共產品或服務,私人投資者期望獲得更多的利潤,而政府則夾在中間左右為難,定價水平難以平衡社會公眾和投資者的利益。
3、缺乏共贏意識
一些地方政府“共贏”意識匱乏,在合作中一再強調自身優勢地位,視自身為社會資本的監督方甚至對立方,缺乏考慮合作伙伴的合理權益,導致社會資本在屢遭挫折后“傷心”“失望”。
中國物業管理協會副秘書長、福建永安集團董事長林常青說,很多地方還是“政府吃肉、企業喝湯”的思維,能源、通訊等高收益項目仍壟斷在政府和國企手里,一些根本不賺錢的項目像卸包袱一樣扔出來給民企做。這種情況不變,大面積PPP合作在現階段就不可能成功。當前大多數地方政府都缺乏基于成本漲跌的調價機制理念,“回報意識”不強。
不僅如此,不少受訪的企業家指出,當前在PPP合作中,一些地方在PPP項目中將社會資本視為“附屬”,在公司架構上“大權獨攬”,在決策上“獨斷專行”,使一些社會資本有“二等公民”的感覺。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國PPP研究院理事長鄭新立認為,在PPP合作中,往往立項、評估、決策完全由政府說了算,企業參與積極性不高,即使形成合作意向,也無法形成現代公司治理模式。
郭建新說:“PPP合作引入社會資本的意義,不僅在于補充資本金不足,更多要形成契約精神,使我們的產權和市場制度更好地適應社會化大生產,進一步打開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潛在空間。視社會資本股權為‘二等股權’的PPP項目長久不了。”
此外,一些地方在引入社會資本后,還不斷對企業提出不合理要求,讓企業承擔本來不應承擔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