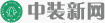每到年底,伴隨著春運的熱鬧,另外一種很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現象也開始上演--農民工討薪。討薪的背后是欠薪,欠薪又稱“拖欠工資”。這一名詞的歷史并不長,最早肇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農民工聚集的建筑業、服務行業和制造業。伴隨著社會的進步,其他行業的欠薪行為已得到很大改觀。然而,建筑業的欠薪依然是行業的普遍現象,成為欠薪的重災區。對此,當前社會對于這一問題的研究一直在繼續,也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當前社會普遍研究結論
關于建筑業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當前社會的普遍結論有三種:
一是,農民工自身權益意識不高。
根據統計,在涉及農民工討薪的案件中,農民工群體有以下幾個共同點,它們分別是:
1、沒有簽訂勞動合同;
2、沒有簽訂工資標準協議;
3、不掌握包工頭和用工單位的基本情況;
4、工資條上沒有包工頭確認簽字。
而上述這些又恰恰是農民工在日后維權中不可缺少的必備資料,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農民工通過正常途徑討薪的難度。
二是,法律制度不完善、執法不嚴。
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2011年,“惡意欠薪”與醉駕一起被寫入刑法修正案,司法機關認定為惡意欠薪的單位和個人最高將被處以七年有期徒刑。但從近年來的實踐來看,兩者發揮的效用截然不同。醉駕入刑后,嚴厲查處了大量酒駕、醉駕行為,形成極大震懾,而打擊“惡意欠薪”的力度還需不斷加大。
吊詭的是,調查顯示,迄今所有被判刑的都是包工頭,更上游的大魚們依然逍遙于外,這是極不正常的現象。似乎開發商和建筑商們特別容易玩“躲貓貓”,把責任全部都分散出去。一旦遭遇到背景強硬的國字號開發商、建筑商,更是微妙。
而且,“惡意欠薪”的標準很難界定,造成“惡意欠薪”入罪執行不暢,給欠薪行為留有不小的法律灰色空間。
三是,建筑業獨特的用工制度——包工制度。
我國相關法律要求,工程項目必須由具備相應資質的建筑企業承建,但在實際運行中,建筑工程中普遍存在這樣的情況與現象,即:總承包-分包-轉包-再轉包,最后將施工項目直接轉包給包工頭個人。一些關系戶只需繳納一筆占工程造價2%-5%的掛靠費,就能借用建筑公司的資質從開發單位承攬工程,然后他們再層層轉手分包。
這種轉包、分包的現象,導致的是債權關系的復雜。由于層層轉包,導致責任主體分離,農民工和用工單位事實上不存在勞動關系,即使跟包工頭,也往往是口頭合同,提供不了正規的勞動關系證明。一旦某個環節資金出現問題,就會形成工資拖欠。
在這層層轉包中,始終處于“生物鏈”最底端的農民工,則被各種復雜的債權關系“推來推去”,致使討薪維權無從著手,像貝殼一樣被晾在沙灘上。
基于以上三種研究結論,十多年來國家和政府出臺的關于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的法律法規政策文件達到200多個,對農民工工資拖欠的政策關注度高于其他任何一個社會問題。但是,即便這樣,仍舊不能解決建筑業農民工工資拖欠的問題。
一份研究報告大膽提出資金墊付是欠薪的根源
2014年12月初,由多所高校“關注新生代農民工計劃”與公益組織聯合發布的《當代建筑業欠薪機制與勞資沖突調研報告》中提出,資金墊付是欠薪的根源。
《報告》認為,之所以遲遲解決不了農民工資拖欠的問題,是因為我們很少注意到地產資本在農民工工資拖欠中所扮演的角色,沒有真正意識到地產商從拿地到銷售整個流程都涉入層層的資金卷入與墊付才是欠薪的根源所在。


根據以上圖表顯示,高達八成的欠薪工地存在資金墊付,商品房、保障房墊資比例最高。
而被人詬病為建筑業潛規則的“層層轉包”,與之相伴的則是資金墊付,以及空手套白狼的可能性。層層分包及由此產生的層層資金墊付,這中手段的高明之處在于:一來緩解資金緊張,二來有效地讓本應承擔勞動用工主體的施工單位在法律意義上變得模糊不清,從而成為建筑資本實現增殖和有效規避責任的有效手段。
其結果是,當在工地出現勞資糾紛和安全事故時,施工責任主體往往是以嫁禍包工制的最基層食利者--包工頭--的方式逃避責任。因為根據調查顯示,勞務分包企業與開發商分列建筑業農民工工資拖欠的前兩名,它們所占比例分別為43.5%與31.2%。我們傳統觀念中所認為的“欠薪包工頭”所占比例僅為13.8%,即便加上“因包工頭無力支付工人工資而討薪”的比例也僅為18.1%。
假使《當代建筑業欠薪機制與勞資沖突調研報告》中關于“資金墊付是欠薪的根源”的觀點是確鑿無疑,那么,欲治理建筑業亂象,必先取消包工制度;欲取消包工制度,必先從源頭上禁止資質掛靠和工程轉包行為;而欲消除掛靠與轉包,則必先消除建筑業監管部門的“權力尋租”機會,加強建筑公司的資質管理,鏟除權力尋租與腐敗的土壤,從根本上減少資金從上到下的層層墊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