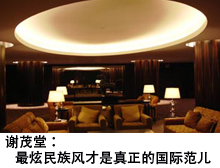"我有幸趕上了中國的室內設計從蹣跚學步到飛速奔跑的發展歷程,并與之同行。"在與中國室內設計共成長的過程中,北京弘高建筑裝飾工程設計有限公司(簡稱弘高)總設計師、第一設計院院長施建民也見證了一家優秀裝飾企業在設計領域探索著成長的發展歷程,并正與其一起努力,共同向世界一流邁進。
轉換
1996年,大學畢業后在新疆當了3年美術老師,后又調到某政府部門宣傳口工作還不到1年的施建民痛下決心,辭職來到北京。
施建民是奔著能到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進修,了卻當時沒能有條件報考重點美院的遺憾的目的來到北京的。"小時候,我爺爺每次見我的時候都說'將來上研究生,爺爺供你上學'。那時并不太懂得'研究生'是干什么的,陰差陽錯上了師范的美術專業之后,才漸漸了解了爺爺奶奶的過去——他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當時的進步青年。那時心底才有種自發的敬畏之心。"
正是這種對知識的敬畏之心,使施建民離開荒廢專業的公務員崗位,勇敢地開始了他的"北漂"生涯。"一路下來接觸了很多新鮮的事物,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從專業應用美術到電腦繪圖,甚至考到北電的攝影專業,那個階段我只感覺到了更多的希望和快樂,感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進入室內設計行業,施建民的起點很高:"是一家雙甲裝飾企業,當時全國的雙甲企業不到10家。并且在那家公司參與的第一個項目就是在建的朝陽門外交部大樓,那種自豪感油然而生。"
施建民說,這份工作對他的人生轉折起到關鍵作用。這個轉折,不僅是身份上的轉換,更多的是心理上轉換。
入職不久,施建民所在的團隊全情投入北京國際金融中心大廈項目的投標,競爭對手是全國的所有雙甲公司。在近40天時間內,整個團隊幾乎沒有休息時間,而施建民也創造了在電腦前連續工作,三天三夜沒合眼的紀錄。
"最后打完圖封完標早上8:00,負責設計的老板送標。我回家,腳是腫的,襪子黏在腳上,一點點剝下來,沒洗就睡了。10:30 BP機響起,回公司開會——我們的設計標僅一票之差位居第二名,未能中標。這意味著全體參與者近2個月的付出都白費了。現實就是這么殘酷。老板舉著圖紙對我們說,設計不中標,這就是手紙一張,當手紙都太硬。這對我的觸動極大。"
那時的施建民還沒到24歲,作為一個被夸獎著長大,還在學校、機關工作過的年輕人,在長時間精神和體力都透支的情況下,辛苦努力的結果被貶的一錢不值,心里落差可想而知。"這件事讓我真正意識到市場競爭的殘酷。"
"搶標"
上世紀90年代末中國的建筑裝飾行業并沒有單獨設計的概念,也很少有設計費,那時的招投標都是設計和施工一體,前期靠設計拿標。因此,雙甲公司的設計部的最大功能就是"搶標",如果沒"搶"到,整個團隊數十天的投入都是打了水漂,不會有任何補償。設計的價值得到社會的認可,一個項目真正能有機會和甲方談設計費,是2000年之后的事。
在這樣殘酷的市場競爭環境下,施建民在轉變,在學習,在成長。1998年2月,一個偶然的機會,施建民加入了弘高裝飾的前身萬順利裝飾公司。
和全國的裝飾公司一樣,當時弘高的裝飾部也就是十來個人,幾臺電腦;然而,和當時的很多裝飾公司不同的是,弘高自成立開始,對設計就十分重視,設計部門的地位、得到的資源都是當時其他裝飾公司的設計部不能比擬的,弘高的設計團隊也十分團結,有戰斗力。
"比如說投一個標,開發人員把標書拿來之后,就不用操心了,我們就知道該怎么按部就班地去做,到點給他送標,肯定沒問題。"施建民說設計師們各司其職、互相促進,"誰的方案做的漂亮,就可以得到大家的一致的贊賞,某個人做得的確很爛,那就是被大家貶,最后大家都是朝那個好的方向去做,做出來大家都很滿意。"
20世紀末21世紀初這幾年,正是國內裝飾行業飛速發展的時期。
在那個時期,施建民和弘高的設計部打了幾場硬仗,在北京乃至全國的裝飾業界樹立了聲名。
讓施建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2000年弘高投標北京移動美惠大廈項目時的情景。這個項目的競標強手林立,競爭的氣氛,施建民用"慘烈"來形容。"我們投入大量的精力,包括方案的設計、制作、裝訂,都特別用心,然后我們何總(弘高董事長何寧)親自出馬去講標,這是在任何其他項目上是沒有的。"這一輪,弘高和另外兩家裝飾公司入圍,他們有一周的時間深化一些重點部分,再拼一輪。這一周,施建民"白天、晚上去做,做出那一套方案。何總,濤總(弘高總經理甄小濤),還有我們當時其他的老總晚上都坐在中間的大堂里邊,也不走,就聊天,等我的這個方案出爐。"在這樣的志在必得下,弘高終于如愿以償。
"我們當時引以為豪的地方是,在那個競標最瘋狂的年代——個標甚至撲上去二三十家,有些可能一次出兩到三套方案——我們帶方案去投標,有些公司聽到弘高去就撤了,不投了。"


感受
"作為設計師應該多去感受。我們在設計每個空間的時候,實際上是在提供一種生活方式,我們需要去體會各種各樣的生活方式。"上世紀90年代,在人們的生活領域,很多新鮮的、高端的事物進入中國,設計師作為這些空間的營造者,首先要自己感受和理解這些東西。
在做他的第一份室內設計工作時,施建民曾被安排設計全日制餐廳,他盡力查閱資料,還騎自行車去當時的五星級酒店看。設計完之后,他的設計主管被老板訓了:"你怎么能讓一個連自助餐都沒吃過的人做全日制餐廳的設計?這不是開玩笑嗎?"施建民說:"那時我真正意識到設計在滿足功能的前提下才能夠去表達你所要傳達的一種生活方式和空間氛圍,否則圖再漂亮,都只是紙上談兵。"
施建民于是定了一個計劃,盡管一個月只有一千多塊錢的工資,他還是每半個月自費去五星級酒店體驗一下。在一年時間,他體驗了北京所有的五星級酒店。
這樣的體驗,也給他在弘高公司后來工作的順利開展奠定了基礎。
1999年,弘高通過競標得到了北京西苑飯店的改造工程,當時,國內幾乎沒有團隊有系統的酒店設計經驗。這個工程,對弘高,對施建民,甚至對甲方而言都是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項目。"當時我才26歲,業主給了我這個機會,公司領導也給我這個機會,濤總也是一起參與。去南方看石材、挑家具,甚至連床頭的壁燈,都是看了很多燈具廠家才定下來的。"就這樣,在沒有系統的酒店設計經驗的情況下,施建民和弘高的設計團隊一起,完成了一座四星級酒店的整個改造過程。
之后,在一次次的"搶標"過程中,施建民的設計能力和設計水平也在飛速提高。
到現在,施建民仍愿意去感受、體驗新的事物、新的領域,這也是設計最吸引他的地方。"我們在接觸一個新的領域的時候,應該感謝業主方給了我們一個這樣的機會,去學習,或者說去做試驗。我們設計師是花
甲方的錢去造自己的夢,造得好,甲方喜歡,我們喜歡,達到這種狀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造得不好,甲方不滿意,我們自己有點自知的會有所內疚。"
正是因為這樣的職業經歷,施建民并不認同所謂的靈光一現,他說設計的靈感應該來源于對生活的感悟和對事物的認知,從自己的閱歷出發,找到跟項目的契合點。因此,他在設計一個項目的時候,通常會回歸到設計的本源。他會問自己一系列的問題:面對的項目到底是什么?想塑造一種什么樣的生活方式?確定一種什么樣的氣質?如何完成呢?"前提是我自己有沒有被自己的想法所打動,自己想到的那種氛圍有沒有感動自己,而并不僅僅是把空間立面體如何做好看的問題。當自己都不曾被自己的設計所打動的時候,怎么有可能去打動客戶呢?"
平臺
施建民一直說自己幸運,幸運地進入第一家公司,遇到了一位嚴厲的老板,使他從一開始就沉著和警醒,不放任自己;也幸運地進入弘高,有了這個可以共同成長的平臺,遇到了很好的領導,獲得了信任和贊賞。然而,他認為最幸運的是,遇上了是中國室內設計飛速發展的大時代,在短短十幾年的時間內,中國成為世界設計師的造夢工廠。


如今,設計已經成為弘高的核心競爭力,以設計領銜為客戶提供服務成為弘高獨特的創新商業模式。在北京東五環外,兩幢辦公樓中的一幢是弘高的設計中心,擁有近300名設計師,由公司直接領導并統一管理。而施建民也成為弘高的總設計師兼第一設計院院長,帶領團隊一起為弘高的未來而奮斗。
"弘高公司成立近20年時間里,注重設計已成為公司的傳統,弘高在業界的知名度及影響力更多地是源于自身的設計實力。我們希望搭建一個屬于設計師的平臺,讓不同能力、階段的設計師都能有一塊適合的土壤扎根成長,高度發揮,施展自己的才華。"施建民說。
設計師一般來說都很有個性,思維活躍,作為團隊的管理者,施建民倡導自我管理,他給自己的管理風格總結了八個字"惜緣,尊重,克己,助人"。
惜緣——人和人相遇、相處是一種緣分,人和人的觀點不同就必然產生碰撞,沒有碰撞就沒有改善。尊重——尊重決定好感,好感決定成敗。克己——勤奮做事,簡單做人。助人——妥協,忍讓,隱藏,授之以余,授之以欲,授之以漁。
弘高設計團隊是一個多元化的團隊,如今還在迅速地發展壯大。"我們弘高的愿景有三條,里面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給員工一個發展和學習的空間。弘高有很多高管都是從員工最基層做起,做到現在,包括我也是,這個本身就可以給員工樹立一個很好的一個目標。"
施建民說弘高設計是一個多元化的團隊,通過不同板塊不同項目,以細胞分裂的方式,不斷發展和培養一批又一批設計師有機會朝自己的目標邁進。
"你努力了,也許很短,半年、一年,你的業績突出,你可能就會先帶領幾個設計師,成立一個所;那再優秀的情況下你的所可以再分類,你可以升級為一
個院。這實際上就灌注了弘高自己的一個基因進去,我們有自己的DNA在血脈里擴張。"
弘高目前已進入到IPO的第三個財年。上市成功的話,弘高的設計品牌將具有更高的價值,更為深遠的影響力,同時也將為設計師提供更好更高更廣的設計平臺,放大格局,放大收入。而施建民和他的設計團隊當下的目標就是扎扎實實地做好每一個項目,不斷提高自己的標準,向國際一流團隊看齊,務實基礎,一步一個腳印的去實現這一理想,在實現自我價值的同時,努力讓公司發展為"受人尊敬
的企業"。